阅读: 63 发表于 2024-07-31 16:56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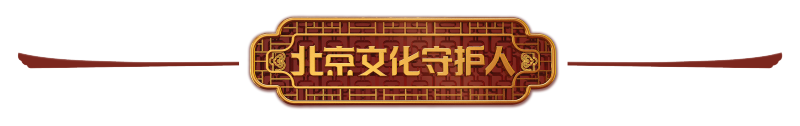


北京文化守护人墙子路轿子坊,北京市密云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,该村有130多年的轿子坊音乐演奏历史,有村民们组成的乐班,上世纪经常受邀在北京顺义、河北兴隆等地演出。近二十年,人们婚礼形式、音乐品位发生改变,轿子坊演出机会逐渐减少,但王树才等老人仍坚守这一非遗技艺,经常在村里公益演出。目前,该村能熟练演奏轿子坊音乐的老人只有五个,平均年龄71岁。

京郊轿子坊的盛况,至少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在农村娶亲时候,三五个鼓着腮吹唢呐、吹笙的乐手,带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,大踏步走在玉米田间路上。十里八乡,都能听见嘹亮的唢呐声。
在北京市密云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,地处北京密云与河北兴隆交界处,是明清两代扼守墙子雄关的一座营城。村里有五位平均年龄71岁的老人,至今仍在传承轿子坊。只不过,轿子坊音乐如今很少在红白喜事场合上演奏了。
68岁的王树才,这支老年乐班最年轻的乐手,也是“墙子路轿子坊音乐”代表性传承人。他觉得轿子坊应该是永远属于乡村的,是最适合在长满庄稼的土地上演奏的,承载了太多乡土记忆。确实,轿子坊是京北传统农村的典型音乐符号,在生活节奏变快的网络时代,它悠扬的曲调弥足珍贵,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长城脚下传统村落,诞生本地轿子坊
墙子路村演奏轿子坊的乐手,普遍的特征是又黑又瘦。王树才笑着说,乐手常年顶着大太阳,一吹就是一天,对体力消耗很大。他介绍,轿子坊本是华北民间给红白喜事演奏乐器的班子。乐手都是农村人,乐器有笙、管子、唢呐、笛、鼓、响板等。

8月11日,王树才在清理乐器,他说乐手常年顶着大太阳,所以又黑又瘦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不是所有华北村庄都有轿子坊乐队,墙子路村有特殊的历史积淀。它位于峡谷地带,山脊上就是古长城防线,有千年屯军历史。村庄至今仍保留着规整布局:庙宇和城门之间,是约六米宽的丁字街道,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民房。村庄南北通透,主路上铺上石砖。
第一次来墙子路村的人,会对村中央的广场印象深刻。红彤彤的大戏台引人注目,隔着石砖铺地的广场,对面是掩映在国槐里的三堂庙大殿。墙子路村每年会组织各类庙会:正月十五火神庙,二月十九观音洞庙,四月二十八药王庙,每次庙会都有上百人组成演出队伍,舞狮子、打快板、舞幡。

8月11日,密云区墙子路村,王树才在村里的戏台前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正因为是塞口之地,村里过去融汇了南腔北调、三教九流,墙子路村是邻近村镇最有名的戏曲汇演地。据公开资料显示,墙子路村轿子坊创立于清末民初,名为王家鼓乐班坊,当时专门经营祭祀、庆典、红白喜事。创始人名叫王景元,班子一共有7人,所奏曲目大多是口传心授,全是工尺谱,有普天咒、一碗水、四上佛、五雷阵等传统曲子,这些曲子至今还在演奏。
轿子坊主要在村里熟人或亲戚之间传承。王树才的师父是本家三叔王恒。王恒在20世纪是远近闻名的轿子坊好手,能连吹唢呐几个小时,经常被北京顺义、河北兴隆等地的人家邀请去吹奏。
王树才小时候,常见三叔捧着笙吹老曲子,摇头晃脑吹一整天后,脸上却看不出疲惫,而是那种颇有成就感的神色。这让王树才很羡慕,他跟着三叔走村串巷,用三年的时间,一边练习乐器,一边看人情世故。在36岁那年,王树才正式成为轿子坊乐手。
从小务农的王树才比较老实,头一回干白事时很紧张,因为他一看见棺材就心里犯怵。他记得,当时用唢呐吹奏了一曲《苏武牧羊》,心里忐忑不安,吹得单调乏味。后来三叔批评他,做这一行要脸皮厚,要拿着乐器敞开了心胸吹,要吹得让人哭、让人笑才能叫好。
王树才说,要干好轿子坊,主要靠自己一个人练。师父的作用有限,只能简单教下乐器怎么用,再者,就是帮徒弟引荐些客户资源。至于是否能凭借技术吃上饭,完全凭徒弟去悟。王树才从业三十多年悟出需要“分寸感”,比如遇到丧事,就要把曲子吹得哀怨些,乐手最好皱着眉毛,表示自己也很难过;而遇到喜事,就要吹得欢快些,最好是挑着眉毛吹,让人感到喜气洋洋。
百年非遗,几位古稀老人传承
77岁的蔡宝库是墙子路村轿子坊乐班年龄最大的乐手,他擅长打鼓、打快板。固定鼓的木头架子,已经用了几十年了,有的榫卯连接处出现松动,榫眼被蔡宝库揉进了纸团。
他和王树才是乐班的主力,两个人也是常年搭档,十多年前曾共同在邻镇连续演奏了三天三夜。

蔡宝库是乐班里年龄最大的乐手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如今,七八个乐手,连轴转演奏三天三夜的盛况,在密云已不复存在。王树才回忆年轻时挑灯吹唢呐的经历,眼里依然有光,“我都不算赶上好时候,我爷爷那时候轿子坊才叫火。他们做一次活儿,要走着吹四五十里地。”
但近几十年来,中国乡村快速进入现代化,很少有人结婚再用轿子了,结婚场地也很少会像传统时候一样,在农家露天院子里举办。轿子坊市场需求急剧萎缩。而随着流行文化的到来,传统乐器与现代人有些疏离,大多数人选择用现代音乐烘托婚礼现场氛围。从城到乡,唢呐和笙的演出需求在消退。
上世纪有段时间,村里轿子坊甚至要散伙了,轿子被人丢弃掉。像王树才这样比较钟情轿子坊的乐手,一度陷入迷茫中。传统民间音乐演奏形式,出路在哪?乡村乐班在时代冲击下,有些无措。在轿子坊低谷时期,很多乐手放弃了轿子坊,进城务工了,也有一些人离世了。王树才和其他几个乐手,一直在墙子路村留守。没有演出的时候,他们就在地头上一块儿练曲子。
68岁的刘学彬,和王树才一样目前是乐班里最年轻的乐手。他家里是乐班集合训练的场所。8月11日,74岁的王志华提着唢呐,步履蹒跚,来到刘学彬家里练唢呐。刘学彬搬出来一把靠背椅让他坐下。王志华身体不好,耳朵有些背,吹起唢呐会时常看着刘学彬等人的表情,他能根据对方表情,判断出演奏的进度。

68岁的刘学彬,和王树才一样目前是乐班里最年轻的乐手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墙子路村轿子坊流传最久也最全的曲谱,就是王树才手上的一本工尺谱。工尺谱是我国汉族传统记谱法之一,因用工、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,源自唐朝时期,属于文字谱的一种。
王树才的曲谱,外皮已经泛黄,用胶带贴了好多层。这本子,是一个村干部1979年送给他的。他用钢笔、铅笔,认真誊写了爷爷、三叔那两代人的曲子。

8月11日,王树才展示他的乐谱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曲谱里有《丢戒指》《送情郎》《小开门》《小看戏》《锔大缸》《马步号》等老曲子,还有《妈妈的吻》《荷塘月色》等新曲子。王树才说,现在不仅红白喜事,有些单位举办文化活动,也会请轿子坊。如果现场年轻人多,那就演奏些流行歌曲。在演奏流行歌曲的时候,王树才有些遗憾,“多好听的曲子,如果三叔在,他肯定吹得比我好。”
2007年6月,轿子坊被密云批准为第一批密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密云区有一年给了王树才5000元作为补助,他在拿到补助的第一时间就是给乐班定做演出服。他打开行李箱,里面整整齐齐叠着8套演出服,服装都是两面穿的,白事穿黑色,喜事反过来就是红色,“虽然我们活动不多,但还是要讲究。”
热爱音乐的老人,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梦想
讲究的不仅是服饰,轿子坊成员们都会自掏腰包添置装备。刘学彬一脸神秘,带记者走进他家东厢房的一间五平方米小屋内,小屋没有光亮,里面物体都用绒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他干瘦的手掀开绒布一角,金属光泽就露了出来,他脸上难掩欣喜,嘴唇微张,像扯动幕布一样,缓缓将绒布拉了下来,架子鼓、电子琴、调音盘出现在眼前。
这是他攒了三个月钱买的架子鼓。他手背上青筋暴起,随手在鼓面上敲出几个鼓点,鼓面和脸部肌肉在同时颤动。短暂体验罢,他脸上露出十分满足的表情,再掀开绒布将乐器覆盖上。他在买架子鼓的时候,是在2010年,当时在工厂大概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,而架子鼓需要将近6000元。让他意外的是,当他把这些家伙买回家的时候,老伴儿竟然特别高兴。
刘学彬家的位置不错,出门是古戏台背面,坐落在南北通衢大道的路东,家里是一道圆形拱门隔开两进院子的庭院。老伴儿在门厅里养了一排花,庭院里全部封上玻璃顶,下面铺上防滑地板。常摆着几把软椅,一张有茶具的桌子,这是刘学彬给常来家里吹拉弹唱的“老哥儿几个”准备的。
他家里一直种着一亩多谷子,早年在附近水泥厂工作,2004年水泥厂停业,他又回家种地,闲时打零工。平时他爱刷网络短视频,跟着短视频学会了架子鼓的打法。他们这个乐班,自学了用唢呐吹出流行音乐《荷塘月色》,“这歌也好听。”刘学彬吹笙的时候,到旋律高潮部分,眼睛便眯成一条缝,随着音乐脑袋轻晃。
王树才家也有一间小屋专门摆放乐器,笙、管子、唢呐、笛、鼓、响板像展品一样,摆放在木桌上。“有个笙是我大哥送给我的,要1000多块,还有一个是村子里奖励我的笙,特别贵,要3000多块。”他言语间露出自豪之色。

8月11日,王树才家中摆放的乐器和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村里很多人家盖了新房,有的还起了新楼,有带花纹的铁门、铺上石地板的院子。但王树才的家在村子一角,瓦和墙面都是老旧的。他家院子里的四分之三都种上了玉米,院里靠墙位置垒了个棚子,喂养了七八只鹅。8月11日,一场雨后,院里土路上泛起泥泞,空气中有动物的腥味。王树才擦拭完笙后,换上一件破旧衣服,薅了把野菜喂鹅,“啾啾啾,来来来。”
65岁的老伴儿王瑞华,裹着头巾,穿了一身印有“环卫”字样的工作服,穿着满是泥点的布鞋,傍晚时分回到院里,汗流满面,王树才接过她汗淋淋的头巾。这一天,王瑞华在邻村里帮忙种树,挣了150块钱。
王树才的人生,一半是现实生活,一半是音乐梦想。他早年可以凭借轿子坊养家糊口,那会儿他凭借吹唢呐的活儿,挣钱盖了西边厢房,供孩子读书。但房子修建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,如今轿子坊几乎失去红白喜事市场,成为地方非遗。他一年的有偿演奏机会不到十次,挣的钱不够换一个新乐器了。
村里成立编辑部,人们自发抢救乡村记忆
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,挂在王树才乐器室的墙上,照片里有几个人或坐或立,都戴着解放帽,鼓腮吹唢呐。这是本世纪初墙子路村轿子坊乐班一起排练时的照片。但王树才叹了口气说,“照片上的人已经有不在的了,还有的半身不遂了。”
失去传统功能后,京郊轿子坊在成为一种民间文化节目。王树才说,有时候,地方的文化馆或者一些企业举办活动,会邀请他们吹唢呐和笙。锣鼓喧天,热闹喜庆,上岁数的人都爱看。
在墙子路村的西边山脚下玉米地里,王树才经常和乐班里其他老人,捧着笙迎着对面青山吹。村里推着自行车的老人,开车的青年人,会被音乐声吸引,停下车子驻足。这时候,看到观众的乐班,吹得更带劲了。
这座青山、长城环绕的村庄,常住人口超一半都60岁以上了,却有别样的生命力。无论冬夏,凌晨四五点钟,总有人早起,沿着房屋后面的山路唱歌、吹唢呐。
将村里故事有意识地收集起来的人,是今年54岁的高克昌。他原在北汽集团从事文化建设工作,2021年来村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村庄面貌极为古朴,但老人们精神矍铄、多才多艺,这两者的反差让他吃惊。

8月11日,密云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,王树才和乐友们站在村里的玉米地旁演奏,高克昌在拍摄视频。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
“这里的故事太多了。人们也非常健谈,尤其是老人,一聊起墙子路的历史,那就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。”高克昌去年5月20日在村里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,主要推送村里老人日常排练的视频图文,里面还有人物传记。他给公众号起了个名字叫“漫话墙子路”。
村里有百年轿子坊,也有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石洞、土丘、城砖、古瓦,每个老人心头都装着不少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:明代的守卒在这里安营扎寨,女真人的铁骑从这里呼啸南下,五星红旗曾在村广场上冉冉升起。那些记忆中,也有平凡与喜庆的日常:一伙男子吹奏唢呐,领着提亲的轿子,风风火火走过乡村土路。
1961年出生的王瑞胜,是“漫话墙子路”编辑部的主笔。他是河北兴隆县六道河镇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师,从1998年起常住在墙子路村。他已经为墙子路村写了近一百篇故事,多是村里的传说。他还为村里11个老人写了“人物传记”,“那些很有特点的村里老人,虽然不是大人物,但一样活得很精彩。”
蔡宝库在王瑞胜笔下,是“死了九次、活了九次”的人。童年时候,蔡宝库和家人在战火里流离,几次遇到炮弹在身旁爆炸;中年承担了过多家务,大病几场,全靠自身素质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,到了晚年遭遇瘫痪,竟然从病床上逐渐康复,现在打起快板不手生,是吹轿子坊和王树才一样熟练的唢呐手。
关于轿子坊的故事,在村里流传不少。王瑞胜从老人记忆和文献中考证,在上世纪20年代,墙子路村就能吸引河北兴隆县的人来看花会。当时墙子路村有三座石头城门高大巍峨,推车的、赶马的、挑担的,人来人往;城里面有踩高跷、说书的;若谁家有喜事,吹轿子坊的乐手带着队伍大踏步走来,会将整个花会氛围推向高潮。
如今墙子路村很安静,即使王树才的唢呐声悠扬地从院里传出来,却烘托得村庄更安静了。村里石板路一天到晚总是空空荡荡,偶尔有慢慢溜达的老人,停下来听会儿唢呐,又慢悠悠地走开了。
但是,没有观众的乐手仍在尽情演奏。王瑞胜回忆,他童年时候经常去墙子路村的姐姐家,再后来,他就索性搬到墙子路村常住。他结识过村里更老一辈的乐手,那会儿王树才还很年轻。墙子路村的一代代乐手,无论是吹轿子坊还是种地干活,总是勤勉踏实努力,凭借自身本事把家人照顾得很好,对陌生人友善热情,这种对生活的热爱,随着轿子坊的乐声一直流传至今。
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王子诚